那封信我改了幾百遍。
那段時間,信封信紙的顏色搭配、紙張的材質,甚至都考慮了。
告訴自己:「顏色和觸感的不同,也許他更能理解心情的變化。」
「這次不提傷害,是不是就不算埋怨了。」
「只寫你過得好不好,不提我好不好,就不會太沉重了吧。」
每次都寫到一半,就覺得——「他應該不會想知道這些。」
於是開始揣測他的反應,想像他讀信時的表情。是皺眉?是嘆氣?每個想像都讓我又多刪幾句話。
最後,還是貼上封條,寫了收件人的名字,飄洋過海。
寄回給自己。
郵戳證明它真的去過遠方。
像某種儀式正式承認……有些話不是沒說,是已經沒有位置說了。
位置這個詞很精確。不是沒有時間,不是沒有機會,是沒有位置。就像一個已經客滿的劇院,即使你有票,也進不去。那些話在門外徘徊,等待一個永遠不會出現的空位。
現在想來,信早已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——
我終於不再重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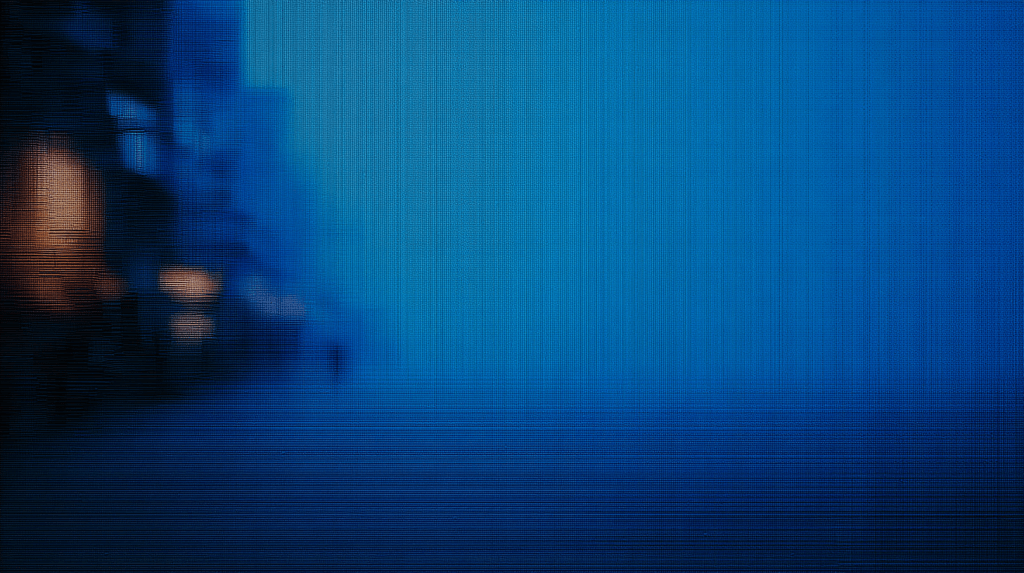

發表留言